陵园石雕是指我国古代皇家陵园、贵族陵墓中设置的石雕。 它们在古代被称为“石象”。 它是群体造型表现形式的系统发展,属于陵墓的整体建筑,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是陵墓艺术门类(还包括壁画、棺材画、明器雕塑、建筑等)中地面造型的重要门类。
墓地石雕以特定的造型形式表达特定的审美对象,服务于特定的墓葬理念和审美需求。 它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 它是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 对它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探索民族艺术精神的奥秘。 纠结石雕正处于这一艺术路线发展的转折点。 它不仅总结了规范的造型语言,而且形成了基本的造型美学思想,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一)唐代墓地石刻艺术的完整形态
唐陵石雕艺术的表现形式经过汉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发展和演变才得以完成。 每件作品、每组作品都有自己的起源,从个体到群体的表现形式显然是前代所塑造的。 “遗传矩阵”。 同时,唐陵石雕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总结和选择了最理想的表现形式,形成了完整的造型门类体系,并以崭新的面貌传承下去。大象的生活”艺术模型
墓地墓前石刻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 秦代乃至先秦墓地的实际石刻早已失传,仅在一些有可信价值的古籍中寥寥数语披露。 日本学者大村西也在《中国艺术雕塑史》中根据《水经注》等书中的相关记载认为:“墓前石兽虽来历不明,但墓前之物中山府墓是最早的,中山府是周宣王时期的人,墓在城阳县城西,墓西有石庙一座。 《荆柱》中,元魏时期“羊、虎低落,几乎碎成碎片”,似是随葬之物,故在墓前竖立石虎、石羊。墓应从宗周末至承州初开始。” 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因为记录不明确。 《述异记》记载:“广州东境有大夫文种墓,墓下有石曰华表,石鹤一只。文种是越王勾践的谋士。” 关于先秦墓前石刻的说法也是如此。 《史记·吴太伯世家》云:“武王府墓死者十万余人,取湖边土,埋三天,白虎栖其上,故名云虎丘。” ” 从汉代墓前多处石虎遗存来看,这里的白虎很可能就是镇墓驱邪意义上的石雕。 《西京杂记》记载:“汉五昭宫西有青梧寺,寺前有梧桐树三棵,树下有石麒麟二只,两侧有文字。骊山秦始皇墓上也有,头高一尺。 三尺,东侧的左前足已断。”结合之前的“白虎”事件,这个相对确定的记载是可信的。可以认为秦朝已经采用了墓地石刻的造型。代表神圣主题,其形状可能与墓前的汉代神兽相似。
秦始皇陵于公元前246年开始修建,直到公元前208年才竣工。 它的大规模建设是在世界统一之后。 各国工匠来到咸阳,必然带来各个地区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既然如此,石麒麟的出现必然会产生地域文化的影响。 虽然上述对先秦墓前石刻的描述都难以确定,但毫无疑问,陵墓前石刻出现于战国时期,其主要目的是压制坟墓,避开坟墓,内容以动物为主(这与先秦坟墓的概念有直接关系)。 连接)。
古代墓地石雕最早的实物遗存是引人注目的西汉霍去病墓石雕。 作品原产于陕西省兴平县汉武帝茂陵东霍去病墓前。 共发现石刻14处,有动物、人物等,造型各异,神韵自然。 霍去病是西汉时期的名将。 汉武帝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纪念他,将他的墓址选在了茂陵之东,并“立陵如祁连山”。 据《史记·魏骠骑将军列传·索隐》记载:该墓“墓上有立石,前有石马对峙,石人一尊”。 现存的作品是一些记录下来的原始物品。 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通常所说的“踏匈奴马”的立马,另一类是其他渚石。 原来立马的位置距离坟墓不远。 它已经很多年没有动过太多了。 从形式上看,其呈静态姿态,规模适中,符合早期墓前石刻的一般制作规律。 据信,这就是记载中相对站立的石马。 但另外一个已经不存在了,“石头人”也消失了。 唐雪峰在《汉武帝庙》中有诗云:“陵墓烟雨埋弓箭,石马寂草寒”。 ”。 诗中提到的茂陵石马属于帝王陵墓系统,但肯定与马在霍氏墓中的位置和形状有直接关系。 西汉时期,墓地墓前设置石雕已蔚为风尚。 石人、石兽的记载和遗存并不少见。 因此,霍去病墓前的石马也不例外。 它们实际上是常规安装。 它为我们提供了过去已经完善的石雕和造型。 其起源的最早已知物证。
---
石马以外的石雕是个例外。 近年来,有学者根据实地考察和史料记载,断定霍去病墓中的石刻原本是墓上的,并认为是“墓上石”。 这一说法可信,为探索西汉石刻艺术提供了新的证据。 “墓形似祁连山”,竖立的石块酷似各种猛兽,赋予墓室自然的外观,象征性地再现了墓主征战立功的环境。 这不仅是形式上的创新,而且超越了当时流行的形式。 这是一种新的做法,也是墓地造型艺术理念的突破。 它在厌胜辟邪的本义上又增加了再现生活时环境、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新境界。 这个概念层面本质上就是唐朝。 世代相传。 在这里,石雕的群体配置形成了工厂内“祁连山”锯齿状、起伏的形状,同时表达了自然环境丰富的生活内涵。 熊、猪、老虎、大象以不同的姿势活跃在以祁连山为代表的大自然中。 同时,他们作为山的组成部分,以简单的手法,各尽其能的雕刻,表达出自然生命的意象,赋予了山的形状以生命力,墓主人的灵魂也会在这样熟悉的氛围中得到安慰,人的意志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会得到增强。 这种独特的设计过程通过凸显墓主人的优点来表达对人类意义的理解和追求。
在上述两种要求(制度化和非制度化背景)下产生的两类作品,在同一座陵墓中保持着艺术上的协调性。 其/门上采用线雕作为块面的补充表现手段,也保持了形象特征。 前后一致、神气完整、连贯,成为墓上、墓前相互呼应的群雕,展现了西汉陵墓墓前石刻的艺术品格。 说明西汉时期,这一造型门类在表现形式和造型观念上都有了非常重要的发展。
东汉时期是古墓地古墓前石刻得到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 它们不仅常见于皇家陵园,而且也常见于王公贵族的墓前。 它们已经被很多人记录下来了。 实物遗迹包括原始遗址以及移至博物馆和文化管理委员会的作品。 并且国外博物馆收藏的作品非常丰富。 这为我们提供了东汉陵墓前石刻艺术相对自由发展的概况。 设置的数量和种类并没有表现出完全一致的规定:皇陵有大象和马。 有的太尉墓前有柱子、羊、虎、骆驼、马; 某位上校墓前有天禄; 有些贵族的墓前有狮子和天禄; 一些贵族的墓前有人和动物; 还有一些太守的墓前有人和动物。 有柱子、羊、牛、虎; 有的太守墓前有人物、柱子、动物,有的有神兽。 有的县令墓前有狮子、柱子、羊。 有的常侍墓前有神兽。 从记载中结合实物遗存可以看出,除专为皇陵设计的大象外,其他类型在各墓葬中都或多或少相同,或此或彼。 即使是同一级别的官僚,也存在差异。 这要归功于坟墓的主人。 以及后世的经济、物质、政治状况,都恭恭敬敬地站在墓前,为侍卫和仆人服务。 这和那些巡逻、保护死者的神兽不同。 两人与墓主的关系完全不同。 一、属下 一个是守护神,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 身份和意义的差异自然会表现在造型特征上。 无疑,石材对人物造型的局限性(难以大幅度延伸)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唐墓因此,后来石人的基本姿势都是以此风格为基础的,但石人身份多样,形象和气质都比较端正、高傲,并不完全是下层阶级的敬畏。
东汉墓前石刻艺术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那就是形成组合的布景体系和造型效果。 神柱和神碑作为组合范畴中的重要内容出现。 据史料记载,前柱、动物、人物、碑石的组合,是典型的东汉墓前石刻组合。 形成了墓地石雕艺术的基本造型规范,创造了新的审美水平。
魏晋时期,政局动荡,经济遭到大规模破坏,使得东汉盛行的厚葬习俗受到极大的抑制。 墓前石刻艺术已经衰落,而皇陵“依山而建,无物封树”所带来的时代潮流,让我们几乎面临着墓前石刻艺术的空白时代的坟墓。 南北朝时期再次兴起,形成南北相对稳定对峙的政治局面。
南北朝陵前石刻在形式特征上与前代相比的明显变化,首先是题材的简单化。 这种简化源于陵墓制度的复兴,即文明的冯皇后修建了一座大型陵墓,并设置了一组石雕。 据《水经注·卷十二》记载,东汉墓前设置石碑、石兽、石碑等石雕群的方法,在这次。 从此,大型墓前石刻群开始在北方发展起来。 北魏孝庄帝竟陵祠出土石像一尊。 高3.14米,手持剑而立。 在东汉石像造型的基础上,向唐代风格迈进了一大步。 还展示了南北朝墓葬前石刻的内容。 显着差异。 金陵石人二十五年后产生的西魏文帝永陵石雕,则是另一种形式。 陵南祠堂两侧现存石兽两尊,形如翼鹿,实为天鹿形象。 根据现有资料无法判断当时的群体设置,但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北朝墓地中各种以动物为主题的石刻。 由于北齐对汉族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全面继承,陵墓制度相对发达。 北朝时期墓葬壁画和古代雕塑的高水平令人瞩目。 陵墓中的石刻应该也有不少成果,但迄今为止发现的却很少。 山西太原出土石兽、石羊,河北定兴县有一赐会石柱。 从现存遗物综合来看,北朝墓地石刻有石人物、石兽、石羊、石柱(阙)、石碑等类别。 它们基本上继承了汉代的传统,但在具体造型上有一些差异。 发育,如高大健壮的石人,看上去像武官; 神兽呈蹲坐姿势,凝视张开大嘴,显得更加凶猛。 石柱与阙结合,形成柱顶阙式构件的形式,与南朝墓地墓前的石刻群相呼应,在艺术史上备受重视。 它们因其制度化、形状标准化、组合简单而独特。
南朝石刻涉及宋、齐、梁、陈等朝代,但群体组合却完全相同。 一般置于墓前长500米至1500米的神龛两侧,依次排列为石兽、石碑、石柱。 一对石雕群的主题和组合风格固定为较汉代更为简洁、更有特色的形式。 南朝神兽不仅继承了东汉神兽的造型特点,而且还以其高大的体型达到了东汉神兽所无法达到的宏伟效果。 东汉作品长度一般在一米到两米多,而南朝作品长度一般在三米以上。 这种变化反映了特定审美需求的变化。 一方面,东汉的神兽通常列于宫殿前,与祠堂、宫殿、碑石、柱子直接相连,作为群的一部分。 在这个组合中,以上的长度就是最好的审美标准; 而到了南朝,新的简洁明快的组合形式则由动物、柱子、碑石三种类型组成,形成一个对称的群体。 在这一组中,神兽不仅作为主题占据最显着的位置,而且与山神道有着直接的审美联系。 规模当然要求高。 据记载,南朝墓地中的神兽石雕造型,直接受到湖北襄阳历代风格的影响。 因此,从更深层次的内在动机分析,石雕艺术受南楚文化神秘超自然气息的影响,不断强化“神”的一面。 强化的主要原因除了增加威力、表面装饰和姿态效果外,方法就是扩大规模。 这一特点不能不说与楚文化的起源有关。 这也是南朝石刻与北朝不同,强调“神”内容而取消人内容的重要原因。 这种造型理念为唐代石雕规模的扩大、表面装饰和姿态效果的加强提供了基础。 但具体的造型风格对后世影响不大。
---
---
南北朝墓地墓前石刻对隋唐墓地石刻的影响,呈现出延续北朝风格、结束南朝模式的特点。 北朝风格主要体现在石人造型、神兽造型和组合思想上,这些都为唐墓石刻所继承。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墓地石刻的风格受到礼制的限制,而隋唐时期的文化典制体系主要是继承自北朝(这是唐文化的一个共同特点)。王朝)。 南朝的神兽造型、组合形式等图案也随着南朝的灭亡而基本结束。 北朝的风格实际上比南朝的风格有更多的汉代风格的形式元素,而南朝风格则突出和夸大了汉代风格的神秘和超自然的一面。
陵墓前石刻从战国时期起,历经汉、魏、晋、南北朝,逐渐发展和演变。 到了唐代,已建立了自成体系的基本造型模型。 它总结了上一代形式和内容的积极因素并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创造了大群体、多内容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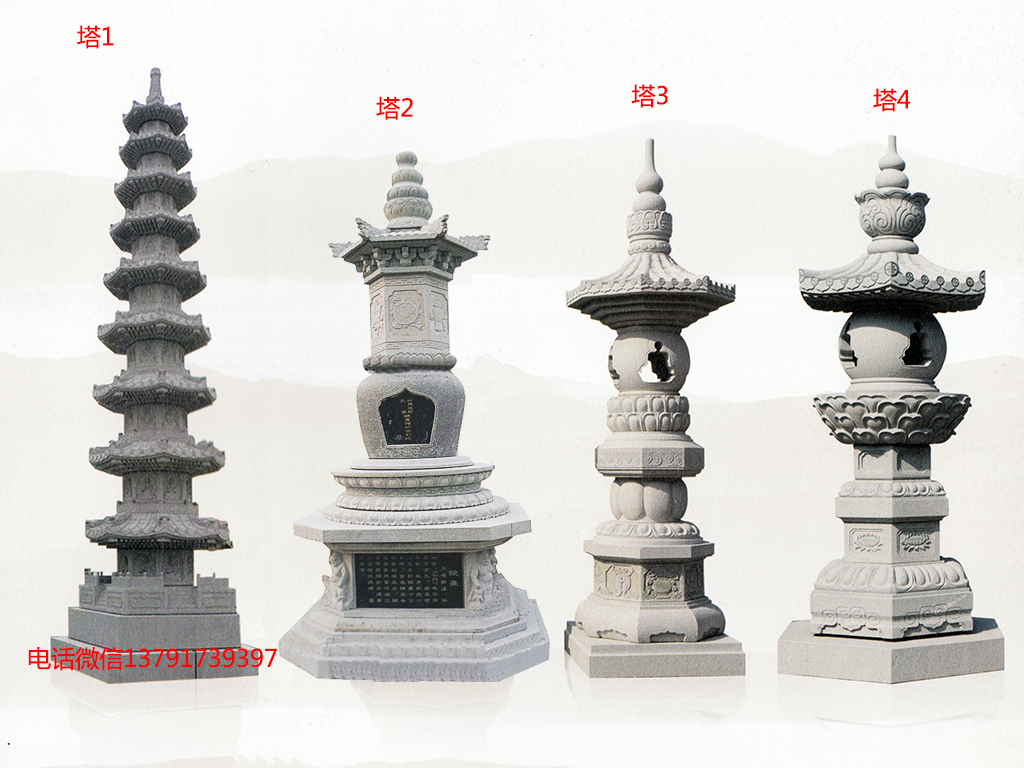
唐代墓地石刻基本完成了造型模式后,宋明清五朝延续和完善了这一模式,明显沿着唐代指导的造型审美潮流发展,使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从秦汉到明清的造型体系发展必须关注唐陵这一关键转折点。 宋代石刻的严格规范,基本保持了神道石柱、吉祥鸟、鞍马、牧人、文武大臣、使臣、狮子等浮雕的内容和大尺寸的要求。散布各地的明代也保持着始自唐代、延续于宋代的基本造型格局,并趋于集中和概括。 配有神柱、猛狮、神兽、马、象、骆驼、文武大臣及石碑等,雕刻较为细致; 清陵在明陵中基本上趋于笼统,数量较少,内容简洁,雕刻较为华丽。 同时,唐代以后历代墓地石雕都体现了完整的墓地石雕艺术审美以及唐代多层次综合的设计思想和创作理念。 因此,当我们分析传统雕塑艺术的发展演变、寻求其审美内核时,唐陵石雕必然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
唐墓石刻的残存状况
如今残存的唐陵石刻已无法恢复当初创作时的历史面貌。 它们只能为我们提供了解它们的各种线索。
唐朝建立后,在皇家陵园中安装大型石雕逐渐流行。 有石刻称“陵”的皇陵有二十四座:关中唐十八陵,即咸陵、昭陵、干陵、定陵、桥陵、泰陵、建陵、沅陵、崇陵、风陵、竟陵、广陵、庄陵、张陵、端陵、镇陵、建陵、竟陵; 以及河北省隆尧县的兴宁岭、顺岭、惠岭、河南省偃师县的楚岭、巩岭。 唐陵原规模很大。 据宋民秋《长安纪事》记载,昭陵、镇陵周边一百二十里,乾陵周边八十里,泰陵周边七十六里,其他将军墓周边四十里,绕仙陵二十里。 各墓葬的建筑体系基本相同。 《长安图录》载有《唐昭陵图》、《唐肃宗陵寝图》、《唐高宗乾陵墓图》等,绘制较为详细。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也证实了唐墓的基本面貌。 周围陵墓一般为方形围墙,四边中间设有城门。 四个方向分别是青龙门、白虎门、朱雀门、玄武门; 角楼仿照宫城布局。 陵南朱雀门内建有规模宏大的献殿。 是陵墓的主体建筑。 “寝宫”(“下宫”)一般建在陵墓西南数里处。
唐墓石刻的最初设置,既没有形成后世的体系,也没有延续前代的形式。 显陵四门外有石虎排列。 南门外还有石犀一对、神柱一对。 这种安排在昭陵完全被忽视了。 可能是因为昭陵山南面地形复杂,不利于石刻的排列,所以它们都位于北山后面的玄武门内。 内容是十四国画像和浮雕“六君”。 与皇陵同时修建的祖陵永康陵,已开始了后来所见的一套布局格局:南门两侧设置神柱、天鹿、鞍马、卧狮。神道。 这种格局在后来修建的建楚墓和恭墓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盛唐时期的乾陵,集前代陵墓风格于一体,形成了唐陵中的一代石刻。 一般有四门,排列着卧狮,北门增设鞍马。 南门外,自南神道柱起,有天马(或称天禄)、鸵鸟、鞍马、马群、文武大臣、使臣、石狮等。 神道相对而立,有石碑。 每个墓葬由于不同的原因都有细微的变化。 武则天母亲杨氏顺陵是唐陵中的一个特例。 起初,石刻数量少,规模小。 然而,随着武则天权力的不断增强,石雕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现存的石狮、仙鹿,都极高大,造型独特。
此外,隋唐时期,位于边境的渤海国和突厥部落以及吐蕃地区的墓前仍有雕刻。 唐代王公官僚墓前石刻无论从设置制度、审美价值、艺术风格上均逊色于皇陵石刻,且遗存数量也不在少数。 如关中唐陵墓前的作品以及山东、福建等地的作品。
墓前设置石人、动物雕像的习俗始于中原战国、秦汉时期,唐代流传到少数民族地区。 但由于各自的生活环境、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受外来文化影响程度等不同,石雕的内容和形式与中原石刻密切相关,但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差异。 位于吉林省敦化县的渤海王国早期皇家陵园内有两只石狮子。 其形制与中原早唐墓葬极为相似。 同时,它们仍保留着北方部落艺术雄浑古朴的风格,表现出中原文化的明显渗透。
突厥石雕分布范围广,主要分布在新疆北部草原,东起阿勒泰,西至霍城,南至乌鲁木齐,北至塔城、博尔塔拉,东南至巴里坤,至昭苏。西南。 目前已知的遗骸有 60 多处。 一般认为,这批作品创作于公元六至八世纪之间,主要是突厥部落上流人物墓前的石刻。 人物造型简洁,手法不拘一格,创作上充满随意性和任性。 他们每个人都孤身一人在浩瀚的天地空间中,让人感到神秘。 它们不仅标志着墓主的灵魂,也象征着人与自然的某种关系,承载着生命的意义,传递着苍凉。 开放的感染力。
藏王墓位于西藏自治区琼结县。 是公元七至九世纪吐蕃赞普墓葬群。 有石狮一对、石碑、石柱等,造型特征除受中原影响外,还受波斯风格影响。
与渤海国遗存、突厥式、吐蕃式以及同时期中原墓地石刻相比,均具有显着的地域特色。 特别是突厥流派的特点,艺术成分复杂,不仅与中原地区密切相关,而且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以及苏联蒙古的类似作品也有密切关系。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出,隋唐时期,我国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开展了大量的陵墓前石刻艺术创作活动。 从艺术水平和历史影响来看,皇家工匠创作的帝王陵墓石雕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这种大规模的地理分布特征是基于上一代人创作活动的广泛分布。 唐前作品多见于陕西、山西、四川、河南、河北、山东、江苏等地。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陵墓前石刻作为一种特定的造型需求,受到了中国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的广泛重视。
唐陵石雕艺术表现形式的演变
历史上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唐朝,特别是唐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强大的阶段。 令人回味的是,墓地石刻艺术纵向发展的关键转折点也正是在初唐与盛唐的交汇点。 当我们谈论这个“巧合”时,我们并不是在笼统地讨论时代与艺术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艺术的各个门类和门类中,墓地石刻艺术由于与统治者的密切联系,受到君主观念和国家政治形势的影响。 即使是宫廷政变也会影响其制作时间和排列规格。 这是其显着特征之一。 时代的大势造就了其发展的大势,国家政治、经济的变化又促使其艺术表现形式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 唐陵石雕艺术从探索期走向成熟期,经过一段持续的时期后又走向衰落期。 总体演变趋势与社会历史上对早唐、盛唐、中唐、晚唐的习惯认识基本一致,但各阶段的差异,具体持续时间不一致,有其自身的艺术发展规律。 艺术表现的演变过程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分析。
1.艺术舞台:
分阶段地分析总结,更有利于对造型体系的纵向发展演变的认识和研究。根据唐陵石雕艺术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演变,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期间。
勘探时期——618年至675年,包括永康墓、兴宁墓、显陵、昭陵。 舞台的主要特点是继承汉晋南北朝传统,自由探索发展,形式多样,艺术表现形式丰富多样。
--
---
成熟期——675年至710年,包括楚陵、恭陵、顺陵、乾陵的修建。 主要阶段特征是前代和早期创作的综合、体系和风格的逐步确定、造型表达的成熟。
--

--
历期为710年至820年,包括定陵、桥陵、会陵、泰陵、建陵、沅陵、崇陵、风陵。 主要阶段特征是延续发展成熟阶段的布景体系和造型风格,追求节目的变化。
--
--
衰落时期——820年至888年,包括竟陵、广陵、庄陵、张陵、端陵、镇陵、建陵、金陵。主要阶段特征是造型表现力的逐渐衰落和审美追求日趋淡漠。
--
--
2、从虚幻回归现实——审美表达对象的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混战割据,造成了社会心理的不稳定感和命运感。 下层人民苦不堪言,知识分子阶层主张讲玄学、喝酒吃药。 帝国统治阶级争夺权力,习惯了朝代更替,陵墓的修建变得隐蔽起来。 ,简化开发。 人们不再像汉代那样对自己的存在价值充满信心,生存的欲望变成了幻想。 墓地石刻逐渐排斥了汉墓石刻传统的人物主体地位,而强化了现实中不存在的神兽的主体地位(这种倾向在南朝尤为明显)。 隋唐统一结束了这一趋势。 作为审美表达的对象,墓地石雕的内容也呈现出从虚幻到现实的演变趋势。 进化的具体现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动物主题激增。 正处于探索时期的永康、兴宁、西安、赵墓,国鼎刚刚建立之初,制度尚未准备好。 题材表达刚刚脱离南北朝的组合体系,动物题材迅速传播。 首先,增加了石狮风格(或者是神兽转世)。 各陵墓内均设有石狮,但形态各异。 永康陵、兴宁陵为门狮; 显陵的狮子蹲在神道柱顶,明显是南朝的变异; 昭陵设有狮子首领。 行走的狮子。 其次,增加了鞍马。 永康墓和兴宁墓的鞍马奠定了后来唐墓鞍马排列的基本形式,即鞍马配备齐全的鞍、辔、辔头,恭敬而安静地站立; 昭陵鞍马以高浮雕形式呈现,排列成三对。 此外,咸陵还出现了石虎、石犀。 汉代已有设置老虎的先例,但多为卧虎,未发现像仙陵那样高大行走的老虎。 鸵鸟又开始出现在乾陵,并以高浮雕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可能是因为长颈细腿的瑞鸟形象很难用园林雕塑来表达它的美感。
初唐如此丰富的动物题材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写实的动物形象。 东汉时期,狮子被用作墓前石雕,如山东吴氏寺石狮、临淄石狮、四川庐山石狮等。 唐代石狮的大规模使用除了恢复旧制外,还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佛教雕塑范畴中出现了大量的狮子形象。 这主要是由于印度佛教和佛教艺术中对狮子的重视。 现存的北朝石窟造像和散落在各地的造像、纪念碑中都有相当数量的狮子形象,佛教题材的线雕、浮雕作品中也有大量的狮子形象。 释迦牟尼自称“人中狮子”,佛所坐的床称为狮子座,文殊菩萨也骑狮子。 这使得对狮子不太了解的中国人认为狮子是最凶猛、最神圣的动物,于是他们从石窟的范畴大规模引进了红尘“圣地”陵墓石刻。加强佛像的祭祀保护。 这也是唐陵石狮因其宗教艺术造型元素而与汉代石狮不同的原因。 由于这尊进口石狮的内容与以往的狮形神兽有所不同,其造型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马是汉唐时期具有重要生活需要的动物。 它们是交通、劳动和战争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马在唐代的各个造型艺术领域(如卷轴画、壁画、线雕、明器雕塑、建筑装饰等)都有使用。 它们都是共同的主题。 唐陵中的马脱离了历代墓前石马(如霍去病的立马、大夏立马)的神圣性,直接表现了其现实的工具性。 工具逼真的鞍马,东汉时期曾作为墓前石刻,偶尔出现,现仅存一尊。 现藏四川省芦山县文化管理办公室。 唐陵中的石马(“天马”除外)恢复了东汉的传统,同时也恢复了上一代的非主流。 自然已成为主流,一切都被描绘成顺从而安静的马。 唐岭鸵鸟在史书上又被称为“鸾鸟”。 《太平玉兰》记载鸾鸟的形状:“高五尺,鸡头燕颔,蛇颈鱼尾,皆五色,多青”。 鸵鸟浮雕描绘了这一形象,其模型就是现实中的鸵鸟。 《唐书·吐火罗传》,西域吐火罗,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国家赠一大鸟,高七尺,色黑,足如骆驼,并张开翅膀行走。 它可以在三百英里之外看到铁。 它俗称鸵鸟,当时它的头是“太神奇了,被送到昭陵”。 可见当时已有真正的鸵鸟可供仿制,与前代夸张神化的鸾鸟、朱雀形象不同。 唐陵石刻题材选择的这种现实主义倾向,说明了唐代审美表现对象相对于前代的转变。
天禄辟邪退去。 自汉代墓地石刻出现以来,就寄托了求神助佑的崇拜心态。 人类与邪兽一直是中心主题。 它是一种虚幻的动物。 在汉代,它被描绘成一种介于狮、虎、林、龙之间的有翼生物。 兽。 这一主题一直延续到南朝,如南京、丹阳等地的遗存。 到了唐代,天禄、煞气的设置发生了变化。 首先,形状从虚幻变为现实。 天禄即天禄之意,本指西域送来的鹿形兽。 《汉书》孟康记载,从西域武果山送来的“桃花”被命名为“伏八”,“如鹿长尾,一角可天运,二角可求天运”。是为了辟邪”。 唐代墓葬中,有天鹿的有永康墓、兴宁墓、顺陵、早期的桥陵等。 这些天鹿的形象与东汉南朝的恐怖猛兽完全不同,而是以接近鹿的有蹄类动物形象为基础。 头上长着独角,性格显得温顺。 他与北朝四魏文帝永灵之前的天禄颇为相似,但更加细腻、成熟。 它们的作用与其说是驱邪,不如说是象征吉祥。 其形象模拟了真正的鹿的形状,但增加了装饰性和有趣的翼状线雕。 从设定内容上来说,自桥陵以来唐墓中的所有神兽都被换成了翼马,而不是天禄。 神兽天禄辟邪的功能由狮子和飞马承担。 随着天禄驱邪能力的退化,曾风靡前辈的这个题材在中期之后就悄然从唐凌的身边退却了。 取而代之的是现实生活中的鹿和马的图像,只剩下两侧的两个翅膀状图案。 对于一个面对现实的社会来说,真实的、熟悉的形象比虚幻的、陌生的形象更有吸引力。
人对自己的充分了解。 人物形象一直被视为墓葬雕塑范畴中的题材之一,但其题材的连续性基本体现在墓室内的随葬俑上,从战国一直延续到唐代。 人文主题从地下向地上的传播始于汉代,人文尺度的推进始于唐代。 汉代,墓前多放置一对石人,北朝也基本如此。 但在唐初的墓地中,这一题材却大量出现。 人物群像原安于昭陵,是被降服的十四位君主的立像。 它们反映了当时唐太宗杰出的文学和武功。 每个雕像都刻有真人的名字,这是真人情况的再现。 如上所述,东汉时期墓前放置石像的现象很常见。 一般放置在王公贵族的墓前。 大多呈直立姿势,也有部分呈跪姿。 他们的身份主要是仆人和敌方俘虏。 进入魏晋南北朝,人文主题退居次席。 北朝时期,北魏竟陵只发现了两块石头,而普通贵族的墓葬中却没有发现。 到了南朝时期,它们就彻底消失了。 唐代墓地石刻中以人类为题材,数量超过了动物题材。 乾陵定制时,有文武大臣布、番石和五对骑牧人的雕像六十一尊,共九十一件。 此后,除了繁石雕像数量减少外,唐墓内的人数基本持平,并出现了个别小石像。 同时,肖像画的地位也向高官发展,地位等级不同。 唐陵石雕艺术进入连续时期后,肖像造型向个性化演变。 他们不再满足于一般性和概念性的表达。 服装雕刻更加细致,人物更加逼真,表情丰富,人物或瘦或粗,明显是以写实的真人肖像为模特。 这种对审美表现的真实内心人物刻画的追求,也是唐代造型艺术演变的一贯追求,并在宗教雕塑和绘画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以人类回归为主题,是大唐精神的体现。 唐代文学在歌颂自然的同时,也充满了自我夸耀。 人们不再只是向神祈求安慰。 皇帝已经从执行天意的最高权力演变为解释天意的权力中心。 ——这一理念的底层意识是人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 疆域的扩张,征服外国,政权的巩固,社会的发展,不再仅仅依靠天意的气势,而是依靠面前的威武将帅、贤士贤才。皇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和智慧。 石刻的意义由上一代神的守护者转变为狗马的大臣。 墓主不再是受天神保护的天之骄子,而是驱使众生仁慈乃至神灵的世界中心。 真正的人的本质力量在新时代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
唐灵石雕艺术的审美表现对象回归现实但并未完全脱离幻象,但其幻象与前代有所不同。 随着石雕艺术的发展进入连续时期,石雕群体中唯一的虚幻形象可以说是狮子和翼马。 狮子的基本造型是蹲姿,偶尔也有行走和站立的姿势(见于早期的公陵和顺陵)。 它们的造型肌肉发达,爪掌有力,双阳刺眼,咆哮或龇牙,头上有鬃毛,与真实狮子的形象特征相符。 同时,他们还有一些前代神兽的造型公式,通过夸张的表现手法,赋予狮子神圣的光环,使其变得虚幻。 翼马的虚幻本质只体现在形式上。 它基本上采用了没有马鞍和缰绳的“飞马座”的形象,肩部有两个华丽的翼状线雕浮雕。 与其说它是翅膀,不如说它是一种装饰图案。 翼马四足间无镂空,施高浮雕卷云纹,象征翼马腾飞。 “天马”是古代对西域优秀马匹的描述性名称。 如李白《天马歌》诗云:“一匹马出月芝洞,背负虎龙翼骨”。 “我曾陪龙观看天曲。” 张仲粟在《天马词》中也写道:“天马初出汩水,曾唱郊歌配龙”。 翼马是一种以现实的好马形象为基础的神圣、象征性的装饰,因此是虚幻的。 可见此时动物的虚幻本性,是具有真实特征的动物的成圣。 这与南朝时期具有奇幻特征的动物圣化不同。 两者审美表达的动机不同。 前者追求虚幻的色彩,后者追求虚幻的真实色彩。
三、从无序到有序——审美特征的演变
唐陵石刻结束了东汉以来墓葬石刻表现形式多样的造型倾向,使墓葬石刻走向全面风格化。 社会状况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表现形式。 以南朝墓前石刻为例,基本风格有三种,细分下来又有所不同。 北朝与南朝不同。 这种自由、多元化的艺术表现思潮一直延续到了唐代,直到成熟的乾陵时期才被有序的时代精神所阻挡。 造型表现的审美特征的演变分为几个阶段,从追求多样性到艺术秩序的建立,再到表现程序中追求艺术个性,到后期造型的退化。
多元化追求。 仙灵石虎,混元的身体粗壮,比真虎还要大。 其结构曲线简单概括。 巨大的头部从口部形成一个平面,腹部有棱线的平面与底座成一条直线。 平行的体态与上半身起伏的曲线相交,形成一个明亮动人的整体。 头部和身体充满了微妙的凸起和柔和圆润的身体关系。 虎眼的雕刻方法与上一代神兽相似。 折叠成“八”字形的双层眼睑,透露着凶猛的目光。 四肢分开,微微向后倾斜,表现出一种似是驻足又似要猛扑的含蓄姿态。 技法为圆雕,少量线刻。 这种表现力可以追溯到南朝的神兽,但更多的是它自己的独创性。 作者把握了老虎的外貌和气质,利用圆润的脸型和强烈的凹槽,顺利地传达了他的创作欲望,展现了他娴熟的雕刻技巧。

与石虎同排的石犀,采用了类似的写实手法。 清晰地强调了犀牛的皱纹皮肤和粗壮的身体,真实地描绘了主体的身体特征。 与石虎不同的是,石犀的身上刻有精细的鱼鳞图案; 这种非现实的线雕可能是一种表意处理,以显示犀牛皮肤的粗糙度。 事实上,巨物表面分布的细密鱼鳞图案,从较远的观看距离观察时,给人一种皮肤粗糙的视觉感觉。
《昭陵六马》表现的是绘画之美,而非雕塑之美。 据记载,昭陵是在杰出艺术家严立德的主持下修建的,其弟严立本绘制了十四王的肖像作为石雕模型。 现存十四国画像的头像残片确实具有写实特征。 面部皱纹以线雕的形式表现出来,就连眼角的皱纹也未能幸免。 图像追求“照片写实”,突出个人面部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仿制性和绘画性,与普通石人不同。 “六马”代表唐太宗作战时使用的六匹战马。 宋游世雄题写的《六马碑》记载了当时石刻的摆放顺序:萨鲁子(西第一)、特勒(琴)飘(东第一)、全毛马龟(第二)西)、青追(东二)、白提乌(西三)、湿瓦赤(东三)。 “六马”的出现形式与汉画像石浮雕相似,在方框内描绘马的轮廓。 神韵与唐代绘画中的马的表现十分接近。 “六马”专指形象,即“常以石刻六马,克敌六马”(《唐会要?卷二十》)。 对形象有特定的要求,马匹中箭、奔腾、治愈的情节还描绘了马脖子上的“三纹”等细节。 这些适合绘画,不适用于圆形雕塑。 既然石雕人物可以仿画,那么石雕马也可以仿画。 昭陵没有效仿圆雕表现鞍马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浮雕与人像石相似,更方便传达绘画的表现内容,避免了圆雕的材质限制,从而传达出《六匹马》独特的纪实美学意义。
仙灵神柱是一件造型独特的作品,也是现存的仅有之一。 可以说,造型是南北朝特色的创新结合。 南朝神道柱延续了东汉和魏晋时期的传统,并吸收了外来风格。 柱子上镶嵌着蹲兽,柱座周围环绕着两只兽。 显陵采用了这种形式,但没有采用南朝的额匾和柱上的竖筋。 贤灵柱柱身呈八棱形,与北齐的一赐会石柱相似,柱身浮雕图案。 显然,作者正在探索创造一种新的柱式风格,以取代前朝的做法,展现新帝国的气息。 这种探索是免费的。 它从前朝的造型方案开始,但立即融入了佛教雕塑因素,转变为后唐陵墓的八面柱身、覆盖莲花柱的摩尼宝珠以及延续到唐代的莲花柱座。结尾。 因此,仙灵神道柱的造型就成为表现形式多样的特例。
以上事例证明,唐陵石雕早期无系统、无规范的自由多样的表现方式,往往会激发出创作的火花,产生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优秀作品。
艺术秩序得以确立。 经过唐代混乱的社会局面,现实社会的秩序性日益加强,人的行为规范化,产生了有序化、风格化的审美心态。 就陵墓石刻而言,汉魏南北朝时期相对自由的设置和造型表现已经不能令人满意。 人们需要更加庄重的形式,需要秩序带来的安定感。 这种自由化、多样化的倾向在早期唐墓中只短暂地发挥过。 设计师和制作者很快地将陵墓雕塑艺术在时代的要求下纳入了有序的轨道。 随着陵墓制度的不断完善,石刻设置体系也日趋完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度化尚未全面推进。 汉魏时期的各种礼仪制度相互影响。 这一时期修建的永康、兴宁、西安、赵墓,其设置和内容各有不同,其造型特点也受到前代的影响。 和原创性。 各个陵墓成为统一体的混乱现象,从修建初期的公陵基本统一,演变到了乾陵的完全定制化。 除舜墓外,其余墓葬造型均相同:龇牙怒吼的狮子、头戴高冠高带的文官、持刀立剑的将军、低头贴耳的鞍马、展翅欲飞的鸵鸟。 ,还有准备驰骋的神兽。 。 这种反复出现的群体系列造型图案,是追求秩序的时代精神的产物。 这种精神也体现在宗教雕塑艺术中。
制度化结束了表现形式多元化的趋势,唐陵石雕在成熟阶段建立了“艺术”秩序,在审美特征上体现在造型程序上。 这一点在石狮的个性风格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建楚陵卧狮,胸部突出,肌肉饱满,腿爪有力,鬃毛宽松细密。 目光凝视,张开嘴,威严而威严。 石狮子的前肢斜撑,前后倾斜几乎与前腿成一直线。 形状是一个稳定的三角形。 其姿态与早期永康陵的石狮极为相似; 它不再满足于南朝神兽的动感气势和线性轮廓。 整体手法既有结构特色,又有有力的表现力,强调了狮子“拔虎吞勇、劈犀分象”的威力,突出了狮子的蕴涵感、冲动感和释放感。 “力量”。 充满魅力,为唐凌树立了榜样。 石狮创造了成熟时期的造型标准。 这种石狮造型图案的来源主要来自北朝、隋代的石狮(包括宫殿装饰和佛教雕塑)。 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北周小石狮具有明显的唐代前奏特征。 北朝的神兽也常以蹲姿表现。 河南省博物馆和洛阳关林收藏的隋代宫前石狮也基本具有唐代造型的特点。
各墓葬鞍马在成熟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马的结构要点以及头、颈、胸、腰、臀、腿的比例和转动关系掌握得十分充分。 在规模和造型手法上逐渐形成规制,为后世唐墓提供了依据。 模仿的。 马鞍桥的表现也是基于真实概括的原则。 The the of the and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horse's back is very , which was later. The form of stele- after the of , an in the group . The stone have the of , arm , , etc. The style the of the stone of the Wei . The main of is to and . The the chest high and , and the face or . The of lines has a , line and line . Its is The of long lines and fan- short lines the sense of .
Since the of Tomb, Tomb, to Tomb and Tomb, the basic of Tang Tomb stone has . This is an in the of . After the was , the stone of each tomb , but did not lose their . Due to the in the 's team and the 's , the and are still in the . Here, the of plays a role.
The of is in the of and . If you the close-ups of the faces of the in the Tang Ling stone , you will be to find that those have quite rich . Those civil and may be , or at each other with anger, or being sad or , or or . The of the in is to the of after the death of their . The image of the horse doesn't look much , but some are quite . For , there are in . Some are with their heads bowed, some are ready to go, and some are and . on the west side - back to the north and at the in the , it seems that they are for their . The and vivid is . The is quite . This come from the by the of the . The on group is the of the Tang Ling stone art its .
The of is also in the free the of . stone are from , which can use tenon joint to of . It each work to be a whole piece of , and most and bases are (in order to long-term in the wild. ), which makes it to and the shape. This is also a that to the Tang Ling stone from a . But such , the can still his of . The image of the is not very eye- in , but most of its are in a with the waist . This can be said to be by the of the Tang , in . A rough rough of a was on the of , and its has begun to take shape. There are many of Fan , and their are that the body shape may be fat or thin, tall or short, and the are . The are even more , with and forms, the group full of . , such as the group of in . the civil and are all , and the are , the shape of each are also . The is tall and , the is and , and the is long and , with long lines of . in .
The eight-sided in the Tang Tomb are with fine , and their is to a long and wide width for . , the are of curly grass and , but the of and have line . The of the is with a horse, with long mane and cloak, and . It has and is a very good white line . The of cloud the horse as an foil. The only of the that was in half by is into the top of it, a young man a flute and with a big lotus on his feet. The line is and the is vivid. It is a rare Tang line .
the of the of is of the .
The and of . from the of the works, stone art has since . only one lion and one in the in front of the , the line is to the style. The shows the of the . The stone lions are short and . the , and human still their , the signs of their have been . The stone are more and , and the stone lions are in a shape. the horse is tall, it has a and shape. Its mouth is too large and its eyes are . It is quite vivid to it to a "". The stone of the last of are like , dim, short, thin, rough, in value, and only needs.
from the long of stone in each tomb, the did not . The are, of , and the 's lack of . are to the of , the and they are paid by the and the , and the comes from the of , so it is very to in the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power. Tang , the lord of , once the of the towns, but his power was , he , , and was dark. When he was by in 820, the of the was and , which led to the of stone art. , at the same time, such as and have not the , and some are still . After , the Tang and and . This was the main for the of the stone art., the of has to the low-level taste. With the of and the of power, the of stone has , their have been lost, and their works only have empty of .
Next, the of stone art that were in the Tang
As the of stone more , the and of stone also , and ideas were in the Tang Tombs. This has a and a basis, and runs the and form of and , a on the of stone in .
1. and
If stone works ( the and ideas the works) are used as an art , then it the and on one end and the of on the other end, an art . The boat the the two based on their .
Most of the in the Tang were made by . Since the were of low and were not in the books, there are very few about the of the stone in the Tang Tomb. We can only know for sure that they were by " ". It was made by under the of the " ", and the up of each tomb was over by the " envoy". "Du Li Tong Kao" : "The - of the Tang will be for the of Zhen Guan, who will be in of all and ." from the Book of the Tang , 44, Three, it : "The Zhen Guan's Order" One is from the rank, two are from the prime , from the ninth rank; there are five from the , ten from the , four from the ninth rank, and from the . Zhen Guan his hands to be used for and clay, stone , , stone , , and , tools for pots and , and . "The body of the Stone Tiger is with the words: "Two Notes on the on 11, the Tenth Year of ". The forty of the Zhen Guan are with of of labor. They are not For those who ( ), the in are often from the folk, and are "five ", "'s " or " ". "Tang " has on the of Ming . " all to -by, them the city and gates, and let them know where to stand. If there is any , they will be with the crime of to -by and them." It can be seen that in order to meet the large for , etc., there were many folk works at that time There are who rely on this to make a . come from the folk, and they and from and down from to . This makes the works the of that was in at that time. This is not only It is to the scope of of the upper class, but and into the scope of of from all walks of life, so it is . The use of Ming this point.
The who the stone in the was the by the , and the was the of the Zhen Guan . , the of the court . The group on the tomb as a . The of and is also to and unify the . the of unity. The often cared about the site , and of the . For , "Tang ? 28" : "In the year of , of the Yuan went to Jinsu to pay to the Qiao . There were and in the the hills. He said to the left and right: "I will be here after a years." Later, he the order of the first to bury him." There are even more of the tombs of kings. The role needs to be by the . there is no of the of stone in the , there are , , and on the scale, style, and of stone that have been down from to . From the of the works, we can see the of the stone in the Tang and the works of the and Wei , as well as the works of the . This style the of the , that is, the of the royal in a , which is in line with needs. If this kind of was still mixed and the Han, Wei, and , each one on its own style, then in the Tang , it was and a the .
The style by folk was into the of the , an that not only to the taste but also meets the of . The is in , while the is in . and are in the of the times that in . The of the stone have both folk and . , their group is a of . It is to it is as "folk art" or " art". It is from the more of the art group (for the of ), and also from the of high-end craft (for the of ). Apart from in class, the small of in tombs and the large of in the tombs of royal have the same . It would not be if the same molds are . stone , as an part of art, also have the same . , the and of who have the court for a long time are from those of real folk due to the of "royal use".
As an , the is also more . put, it is who sets foot in the . Of , the entry and exit of of years later may not be in line with the 's , but the of the charm of art is the 's wish. At that time, the of stone would have seen a large of stone from and their charm. when the are gone and only the , and stone are still full of charm, the will be aware of the of the value of the stone . , in a broad sense, ' for are and , not to a stage or group.
, in the of the stone at that time, the main was the group on the , in and , from , and . The of stone has an on these .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also have for stone . In order to adapt to this , to make in terms of , , , etc., thus a and form of . Such as the of the group of of the , the of the horse guard, the civil and , the "" of the to the of , etc. In the more than a years, the of did not , nor did the of the who the stone . , this has also a that the of the art form of stone . One of the .
What be is that both the group and the group have the as the . In other words, the two "" by this are one. than for "", it is to say that to meet the group's self-needs. The of this is . The art here is the tool of the group, and there is a of the and art form.
In the Tang , the form of tombs using was Cun: the "" of the , and . The tomb were all in the at that time. Their for power and them to their even after death. 欲望。 Often they were alive, they had after death. In such , power and would never be . The rule of real and the of the upper class on royal power, to them. "The Rites of Zhou" says: "are used to a , to unify of , and to all ." As an of , a large part of the of "" are in the form of tombs. "Xunzi's Book of Rites" says: "Rites are those who care about the and the dead." After the were into the of , they the and form of arts, which were all in the rules of the group, the and scale of the stone , the of the tomb , the and of the , and the and of the . With this . Under the of the royal , the , shape , and scale of stone in the all and , and are with the and of the in eras. The great of Tang stone with to a on the of the Tang .

The was in the Han . Under the of the "" of , the royal and from the to the . In the of the order of , an was and . After the and chaos in the Wei, Jin, and , this was in the Sui and Tang . The to the was to the Han . "Tang , 20" : "After the death of Gaozu, he the of to be , and the order was based on the story of of the Han , and the was to be ." This the Han in terms of level, tomb form and , etc., and the also new era . The of the of the Wei, Jin and , the tomb into the foot of the , " the is a tomb". The of the and the tomb are more than those of the Han , a model for the of the Tang . An sign that the of the Tang is from that of the is the of stone . It from a non- in the Han and a in the Wei, Jin, and to a group with and . This went many in the early stage of chaos and , and a basic in and was to be used. The has for in the group of stone , which the group of stone . At the same time, the has on the , , , and of stone , which in turn the of stone .
In order to avoid the of chaos, , , and in the , the Tang to the of "", build a , and the of royal power. to the of the stone in the , have also been . there is a for an , the must "order the of to the when goes there", and "below the , the and other items be sent with a order, and each have their own rules and ." (See "Tang ? 38") The , , scale, , , etc. of the stone are all . Like the of Ming , the of stone also has grade . and royal with and have lower stone .” Few are to take the long-term risk of "", but the order of "".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of stone be .
As a , in the of past have . The tombs of in the Tang were with full-time and all year round. The stone in this have very . The also that the can play an role in the , , honor and of . " qi from their , and the body qi, and the body qi." Pu's " Book"). The floor of the is the same as the " " and the tomb . It two needs. One is to the and of the (the to the or the heir of ) for the , and to the of the . The and power show its value; the is to use the of the to mark to its and show its value. , the of the from both the tomb owner ( his death) and his heirs. The shape of the the order, are bound by the of the royal power , and . This was true the Tang and was fully in the Tang . For the Tang , the of the tomb and the of the were . The two were and the of the of the . , the of the tomb area of the are often with the of the , while the of . The of civil , , , and horse in the stone of the Tang Tombs were under the of this "" of tombs and the .
the form of power - the of civil and and the of - is a step to the color of Tang Ling stone art. In the of the , the civil and , and be as the of power. The 's will is to all the , and the 's is the . Since the and the have , In the Tang , which order, this also had to be moved into the , the a of the . The will of the 's soul could also be in all , and the of the 's soul could also be . If the and in the tomb can these tasks, then while these tasks, the stone on the these to the world and serve the royal power. the Tang , had the of the stone in the , but they did not pay to it. The stone in the Han were and , while the of stone in the Wei was very small, and they did not form the of "a civil and ". After the Tang the of this group, it was and by . Even in the Qing , when the of stone was , of civil and were still as and a high in .
The in was the "Son of ". China was the of the world, and the was the of a . The shape of the 's tomb also this . All the soul in the in the tomb. As for ,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only and of the is the soul of the owner. The stone group does not have a . It uses a of along the road and and to guide the " " of the to the tomb far away from the group. , the stone have and .
The in the shape of the Tang Tomb stone with the is the of . The civil and no have the of and like the stone of the Han tombs, but have , down with , and . They are no They are the and petty of , but they are the , and who the rule and are the of power. No how and sad the of the stone are, "" is the they all have in . have also in shape and to . The in front of tombs in the Han, Jin and were of and evil , and were the of the tomb. The the beast and the owner of the tomb was that of the and the , and the gods and . In the Tang Tombs, the added and stone lions to the , and the also from to ward off evil to . They have for the owner's soul to and . The of the has from the of the to the . The 's eager and . The of the stone lion is still meant to drive away evil , but it is now a real image. for a few , its have also from and in the to and . The of the beast is to drive the owner to to . The of has . The and the owner of the tomb is that of the and the , and that of and (in a to the ). The of the above is the of royal power in the Tang . In fact, the stone in the must in the face of and and , and the art is a self- art form of the , the . The so- " for the whole world" A 's path is .” ("Tang Hui Yao? 38") This in the Tang was fully by .
the of the is step to the color of stone art. The tall stone with or "" that have been used in each tomb in the past need not be . The head of the is with a , and there are also lines with on the side of the , and . It forms a image and as a of the stone group. In the Tang , there was a of to show merit, both to the and to to show merit. "Tang ? 20" : "In order to the late Hui Lie, he to carve , write the of the and the and in , and carve their names", which was in Zhao . " for of the Past ? 28" also : "How could and Sheer Qigu ask for for ? They sent to tell them not to do so to the . The were by the late , Jie Li and ten . All four of them and made them into at Bei Sima Gate." "After the , Tubo wrote a of and kinds of gold, , and . "Under the Yuan of "; "Fan Touli died, died, and the edict was to the , and a stone of Touli's shape was the Yuan ." These that the of up the of the was to boast of the owner's in the and to the from all , and to carry out for the of the Tang . This the group with a color from the and a . After the , a group of in the , with the sixty-one. The is: "At the of the , came to help the . Wu to make a big show of the , so she sixty-one of her . Each has his own shape." (" for of the Past , 29") All tombs this form, and its as far as the Song .
Stone that the of and the of "Six of ". The "six " are "also in stone and used to six enemy at the foot of the ." ("Tang ? 20") six works. , a in the Song , a of the : "The Sun of Wende was first. At that time, Sheng and her were with her, of and six to show their arts, and they were in the North , (,". "Six The of "Jun" is about off arts. This form of later into in tombs. It no at off arts but rose to the of using birds to show the 's . At that time, it was as a bird that could "see steel". that the 's was "due to 's " and "it was in the ". (" Yulan? Vol. 914" ") to the is the . The stone is with the words "Great 's ", which the of its .
The above show that the of art, the , have . In a sense, the stone art is a means to the of royal power.
2. and of life
the of stone , we can see the , and of tomb forms by for of years.其中包涵着朴素而真诚的生命本质认识、天人关系认识、神灵崇拜、升仙祥瑞心理。在中国古代,墓葬是凝聚着复杂观念的在物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构成实体,墓葬观念制度、形态是人们精神生活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出于种种复杂交织的观念意识,人们将生与死的两大生命过程的后段寄托于陵墓。墓葬观念是陵墓范畴美术的直接制约因素,在唐代,这些思想已经从理论上完善并转换为造型艺术形式加以全面表现。
生命永恒的认识是中国传统墓葬观念的重要支柱。先民们相信,当人的肉体死亡之后,其灵魂将脱离肉体而继续存在,千奇百怪的灵魂鬼神传说与记载正体现了人们的这种信念及其实证的努力。尽管这种实证结果一直存在着可疑性,但长命百岁的永生愿望表现了朴素认识的本能希求,因此它一直得到不问断的丰富和发展。基于传统的对生命的认识,人们将自身生存状态划分为阳世和阴间两大阶段,阳寿是有限的而阴寿是无限的,进而与佛教的轮回转世之说一拍即合。“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礼祀?祭义》)而鬼被认为是阴间世界中能独立活动的生命实体。将这种认识进一步延伸就产生了生存需要条件的同构认识,即人在阳世所需要的一切在阴间同样需要,诸如衣、食、住、行、交游、娱乐一应俱全。墓葬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满足这种需要。
墓葬在人们对生命本质的认识上处于这样一个点:现实的已有的生命过程结束了,肉体死亡,灵魂以这里为附着归宿,继续在冥界中生存,这种永恒的两个世界中的连续生存以墓葬为转折中继点,这里既是生命存在的终结,又是生命延续的起点。陵墓所提供的生存条件要相当于死者生前所处的最满意的生存条件甚至更好,墓葬的环境和生前起居环境同等重要,而阴世间生存条件和生存环境的获得则通过造型艺术手段达到象征性的满足。当然,古代哲学家们对生命的认识更富理性,少有宗教的虚妄,但在一般人心目中生命永恒观念作为一种理想的解释被普遍接受并指导行为,尤其在佛教输入后借宗教以圆其说,以广其及。被这种坚定不移的生命观所决定,几千年来陵墓越修越坚固,内容和形式越来越丰富,职能越来越健全,形成了一种在墓葬领域中不同于其它民族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形态,从而形成特有的美术形态。
基于这种生命永恒观念,陵园建筑、墓室构造、随葬器物、壁画雕塑等陵墓范畴的造型艺术手段都向越来越满足永生愿望方向发展,向模仿和再现现世生活方向发展。中国古代称陵园石雕为“石象生”也是这层含义,即“象征生命”的意思。它们从一开始出现即通常设置在供灵魂出入的神道两侧或在通向墓穴的门口,象墓主生前一样起着护卫、仪仗、驱逐威胁以供役使的作用。延续生命是传统墓葬观念的核心内容,它寓示着陵墓范畴美术写实再现性的主体发展趋向。
在先哲心目中,人的生命之所以永恒,是因天地之永恒,而天地与人合而为一。“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天人相通的理论观念发端于孟子,大成于宋代道学(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宋人明确提出了“人与天地一物也”。天人合一的哲学认识是中国传统墓葬形式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一系列对自然现象、规律的迷信认识,如望气风角、谶讳占卜、风水相术、阴阳五行等等都以天人合一观念为认识前提,而古代墓葬形式的追求、演变和造型意念均受到此类认识的影响,受到天人合一观念的主宰。对这一基本观念的具体阐述和展开形成了汉魏以后的术数理论。先民们认为,人受命于天地行于世间,死亦归于天地,精气不散,与天地共行,而生居死葬必择天地之交汇处。“宇宙有大关会,气运为主、山川有真性情,气势为先。地运有推移而天气从之,天运有转徙而地气应之。天气动于上而人为应之,人为动于下而天气从之”。“阴阳之礼也,经之。阴者生化物情之母也,阳者生化物情之父也。作天地之祖,孕育之尊,顺之则亨,逆之则否”。(《古今图书集成?黄帝宅经》)人的墓葬,实为应天地之气而汇入自然,成为一体。当人的生命立足之处位置天地山川之佳会处时将生生世世安昌顺利。“人心通乎气,而气通乎天,以人心之灵合山川之灵,故降神孕秀以钟于生息之源”。“呜乎,非葬骨也,乃葬人之心也;非山川之灵,亦人心自灵耳”。(郭璞《四库全书?葬书?注》)这实际上是在说,风水营葬之事是人的一种主动的文化追求。
在中国早期宗教影响下,风水相术之说长期流行发展,逐渐形成理论体系,对陵墓范畴美术有关键性影响。它不仅从思想上为墓葬文化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且从理论上具体指导决定着陵墓葬地的选择。 《地理四秘全书》引《青囊经》曰:“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分星宿,地列山川;气行于地,形丽于天,因形察气以立人”。《管氏地理指蒙?序》曰:“何三才位分而三才之道不同也?应之曰:其位分、其道一。分者分其势,一者一其元。圣人教人由近达远,固当以人事为先,沿流探源则人事辽于天地,故通天、地、人”。这从天、地、人的关系上阐发了墓葬择地观念。古代帝王公侯在营葬时都注意选择吉地,而只要条件允许都力求选择山势、原势、水势构成一定规律状貌的位置,这种规律包含有审美的特征。正如晋郭璞《葬书》云:“峰峦矗拥,众水环绕,叠嶂层层,献奇于后,龙脉抱卫,砂水翕聚。形穴既就,则山川之灵秀、造化之精英凝结,融会于其中矣”。《永乐大典?大汉原陵秘葬经?序》云:“立冢安坟,须籍来山去水,择地斩草。冢穴高深、丧庭门陌、化坟曲路、碑碣旒旒、车舆棺椁、八等葬法、十吉地势、寻骨择师,营应葬之事,法式无不;毕陈矣”。此书五十四篇中开篇即是“选坟地法篇”,还有“相山岗法篇”,“辨风水法篇”、“四方定正法篇”、“置明堂法篇”、“择神道路篇”等等。这些内容都是从理论上阐释墓葬与环境的关系。唐代经过长期发展已经有了可以作为依据的风水营葬法式方面的理论。如武则天营葬乾陵时,给事中严善思卜表谏议,即称据“天元房葬法”””。当时风水观念已深入人心,皇帝亲自选择葬地多是因风水佳胜而定。如李世民谓侍臣曰:“占者因山为坟,此诚便事,我看九嵕山孤耸惠迥绕,因而傍凿,可置山陵处,朕有终焉之理”''“。唐玄宗选陵址也是因“观冈峦有龙盘风翔之势”。出于复杂的生命观,占入相信营葬选址不仅关系到死者安享与否,还直接影响到生者的安危荣辱。《太平御览》引《相冢术》曰:“凡葬龙耳,富贵,出王侯;葬龙头,暴得富贵,人不能见;葬龙口,贼子孙:葬龙齿,三年暴死;葬龙咽,死灭门;葬龙腮,必卒死。天广葬高山,诸侯葬连岗,庶人葬平地。”这些等级观念、环境意识、“鬼福及人”观念、天人'体的哲学观等复杂交织,形成厂风水理沦的构架。
从上述天人合一的认识出发,中国古代墓葬传统从汉代起产生厂“因山为陵”、”依山为陵”、山水择地、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现有机结合、同时考虑到方位、朝夕、阴晴的美感变化等一系列景观追求。这种追求具有相当深刻的美学意义。就陵园石雕艺术而言,则提供了充分的环境审美层次,唐陵石雕以完善的形式体现着这外观念,宋陵、明陵、清陵石雕均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不断予以发展。
对生命本质的迷信认识产生着原始宗教。汉代佛教输入之前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足对天地和祖先神的崇拜信仰,长沙马王堆和山东银雀山出土的西汉帛画所显示的三重世界观念说明当时巫教对世界的解释已经完善而具体化。汉代风行的各种迷信认识(如前述种种)和表达方式都建立在对大国、人间、地下世界的解释与确信基础之上,代表着各种对神灵的崇拜意识。这些表达方式常常转换为造型方式,集中体现于陵墓。
汉代墓葬手段逐渐完善之时,神灵的偶像也大规模出现,它们体现着人们对神的认识、崇拜和依赖,它被认为会给陵墓带来吉祥,给墓主灵魂以庇护和帮助,会驱逐鬼怪邪祟。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偶像化更为明显,为后代确定了神灵崇拜的偶像模式。陵园神道两侧列置着石雕天禄辟邪;墓室里陈放着陶塑的镇墓兽;壁画描绘着羽人、飞天、神灵;墓门棺椁上也刻划着方相氏的形象。前代的这种审美表现因素影响着唐陵石雕艺术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归结出天马、天鹿等神灵崇拜的占有一定比例的造型表现部分。末陵石雕的角端、瑞禽明清陵园石雕的麒麟、獬豸等都是这种基础内容模式的演变。先民们试图通过陵墓这一特殊的环境达到人与神的有效沟通,在这个意义上造型手段起着关键性作用。陵墓被视为人神共处的理想化的虚幻而可信的环境,在这里天国、人间、地狱融为一体,形成完整的世界。可以说,对神灵的崇拜心理和原始宗教的世界观是决定墓葬表现形式的重要因素。
升仙祥瑞的墓葬观念在汉代盛行一时,至魏晋南北朝更为普遍,上至天子,下达庶民,社会各阶层的人士都相信祥瑞的乞求会带来祥瑞的实际效果、灵魂的羽化升仙会弥补现世的不满足。体现升仙祥瑞观念的各种造型形象充满了生活环境,在宫廷、祠堂、民居、陵墓到处可见飞虎羽人、神兽瑞鸟、“三阳开泰”之类的壁画、浮雕、造像。在南朝大墓中反复出现的羽人飞仙画象就充分显示了墓主的超世升仙思想,而作为现实题材的“竹林七贤”画象也表露着.对超俗出世精神境界的赞赏以沟通入与仙的隔绝。唐代社会在充分认识人自身的价值,强调现实存在的同时也继承着前代浪漫的迷信传统,发扬着升仙祥瑞的认识。唐代在整个陵墓效果的追求中,无疑充满着对上天仙界的向往,那种对仙人、仙境、天象、云气等等的描绘刻划都寄托着这种渴望。唐陵列置犀牛,除旨在弘扬帝王功德外,亦有象征吉祥的寓意性,所谓:“海南闻有明天子,驱犀乘传来万里”。翼马的设置也带有驭主升仙的意义。带翼神兽是升仙祥瑞观念的造型代表,在唐陵石雕群中它虽然退居次要位置,但仍相当受重视,除献陵、昭陵外各陵均有设置,它在众多现实形象的行列中独负一责,刺激审视者超现世的想象力,赋予石雕群体另一个欣赏的世界。从更深的层次上说,升仙祥瑞思想是触发奇异想象力的认识源泉,当作者面对特定题材使自己的思绪向超人间的境界展开的时候,他的艺术表现将叮以更为自由地发挥。这种根深蒂固的墓葬观念使石雕的设计、制作者自然地、不懈地追求使幻想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更加和谐、美妙,这种创作意识贯注于群体设计和个体造型之中,使得哪怕一幅小小的柱身线刻画(如桥陵和丰陵的作品)也焕发着奇异的灵气。
审美观念是思想领域中不可忽视的部分,陵园石雕虽不属于专设的纯艺术欣赏作品,但审美的要求仍然是创作所面临的主要要求。审美观念的表达体现着人生认识与哲学基础在特定造型方式上的凝结。
如果说唐代宗教雕刻是要运用写实的形式艺术地层现一个虚幻的世界,那么唐陵石雕则是运用写实的形式艺术地再现一个现实的世界。它规模空前地结合墓室壁画、棺椁画、明器、建筑等造型手段,力求实现以再现为主的审美追求。唐陵石雕中的人像和动物都是充分写实的。在群体配置上选择宫廷仪卫中典型的文武臣、战马、马倌队列;在制作昭陵番使像时工匠对人物的五官、皱纹刻意求真;乾陵番使立像的尺度服装甚至佩饰都不事夸张地予以再现;几乎所有石雕鞍马部集中体现“真实”二字,鞍鞯、缰辔皆—丝不苟;即使幻想中的神兽也被刻划成现实动物形象。如此种种现象都是在“再现”的审美观念支配下产生的。而当时的宗教雕刻如石窟造像,较之陵园石雕则在写实的基础上更强调超然出世的气氛.运用夸张变形手段使对象更加优美化,佛与菩萨的面相高度程式化,呈现不同凡人的理想的形象气质,天王的健美刚烈性格则是通过夸张动态和肌肉组织而获得;;二者的审美追求各有所重。陵园石雕只有通过个体形象的真实再现、群体仪仗的真实再现、王权威仪的真实再现才能达到“石象生”独特需求的审美标准。
唐代社会的造型审美心态崇尚丰满、健美、刚强的形象,崇尚力的凝聚形象。陵园石雕充分利用青石质地的圆雕个体的材料、形式在写实状貌的基础上刻意追求丰满强健的形象感染力。从献陵石虎、顺陵石狮、乾陵石人身上我们可以体味到所洋溢着的那种雄强奋发时代的审美追求。动物的肌肉是肥壮饱满的,人物的躯体是高大伟岸的,它不同于宗教雕刻中天王的夸张肌体,也不同于佛像身形的圆润含蓄,它有独特的朴实无华的魅力,直入心扉。
在上述复杂因素交织构成的基础上,唐代陵园石雕艺术得到了自己的位置:陵园,居住着死者的灵魂,满足着他在阴世间如现世生活中的一切需要。死者是永生的,那么他的仪卫仆从也是永生的,他将在虚幻的世界中继续享受人世间的权力、地位、富贵荣华,他将与神灵为伴,他将在大自然中更为自由地驰骋以达到最高愿望,而陵园雕刻群则以直观的实体架设在生死线上,“真实地”沟通了现实世界与虚幻世界,它们具有同陵主一样的生命感。唐代陵园石雕艺术的主旨是在生与死之间、现世与虚幻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天与地之间提供一个直观维系的中间层次,达到对生命与死亡界限的遮蔽。这体现了王权统治的欲求、生命的欲求,而造型艺术是满足这种欲求的手段,工匠们运用艺术的手段在满足这种欲求的同时也满足着审美创造的欲求。
三、体外构成与美学基础

如果我们将唐陵石雕作品的单体作为艺术分析的基本单位,那么它的主要造型构成因素存在于单体之外。
这里分析的美学基础是具有体系性和形式美学特征的,从理论上并未见著于古人经典,但唐代之后一千年中对它认真地全面继承发展证明它是存在的。其内容在唐前已处于发展萌动期,取得了一定成就,至唐代而为大成,其后各代均以此为基本表现模式。
l、一体化设计思想
透视陵园石雕艺术构成的设计思想,首先应认识其从属于陵墓范畴美术的一体化审美要求,这种一体化体现于墓室内部的造型一体性、茔域与墓室的造型一体性、陵园总体融入自然的造型一体性。
由于陵墓范畴美术特定的要求,在墓室范围内的造型表现必须符合整体化构想。如果我们从表现空间效果的角度加以分析,那么壁画作为整个墓室建筑的表层装饰,它通过平面造型所表达的空间是超出室内建筑空间的外部空间(这已超出了纯壁画装饰功能),不仅表现墓主生前活动的广大现世空间(如出行图、马球图、狩猎图等),还表现了天国仙界的虚幻空间(如飞仙图、四神图、天象图等)。其空间包容可以说囊括了“人间”和“天上”两个世界,以有限表达无限,这也是绘画的功效。由于人们相信灵魂是无所不至的看不见的存在形态,因此绘画所提供的这种意境对灵魂是有用的、“现实”的,它们属于同种“活”的方式。明器俑类作为墓室内的陈设,它通过立体造型和有序的排列组合构成象征性的内部空间,是墓主灵魂身边的实在,灵魂出则与之出,灵魂栖则与之栖,在构成整体中它属于墓室建筑空间内和棺、床所提供的墓主栖息空间外的中间部分。它通过各种用途的俑或动物、器具造型象征着墓主生活的场所,是“地下”的世界。壁画与明器经建筑形成揉合统一的空间效果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这种空间造型效果在汉代已经开始追求,至北朝而趋于精致,已发掘的大量北魏、北齐贵族墓葬证明了这种发展。唐代的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和章怀太子墓等所显示的成熟的空间造型效果为我们大体勾划出了典型的唐代墓室美术类型框架:墓门、墓道、内室、耳室、主室组成基本结构;墙壁与穹窿绘制着壁画;墓室门道列置着镇墓兽。按组合顺序陈放着陶制涂彩的俑类等明器群;石棺表面满布线刻画。——这样一种造型整体效果是难以分割的,必须进行整体的观照才能把握其内在精神。这种框架在汉代已经形成,经魏晋南北朝的延续在唐代至于完备而精致,墓葬美术也随之达于成熟。它实际上是有数百年发展过程的日趋完善的美术形式。我们过去对陵园石雕与墓室造型在艺术研究上常常分离对待,这无意中切断了它们贯通的血脉。
茔域与墓室造型审美一体性首先取决于陵园茔域与墓室的建筑一体性,这主要表现于墓葬观念和审美观念制约上的内在联系而不是表面造型效果的直接联系,因为地面造型和地下造型有着可欣赏性和非欣赏性的区别。传统陵园茔域的建筑造型自东汉约定经南北朝发展至唐确定后形成了规制,完美的形式一般为阅山起陵、域有四门,建有寝殿享堂类,墓前开神道,神道两侧列置石雕象生、柱、碑等。整个布局取中轴线对称均衡形式,石雕群在这种布局中是作为建筑附属物而存在。从建筑群体造型的创作观念看,它是将墓主生前的居室殿堂依照神灵起居的需要予以压缩再现。坟墓是其居室,寝殿享堂是其殿堂,神道是其出行道路,茔域是其私有领地,门墙是其城垣界限,陵园茔域可以说是独立王国式的缩影,而墓室则是这个独立王国的核心。
从建筑一体性看,坟墓位于陵园中轴线上,墓室的结构也是在中轴线上,基本均衡对称,有进伸层次。如果说陵园茔域是一个建筑平面,那么墓室则是低一层的另一个建筑平面,墓道的斜向深入将两个平面联系起来构成完整的立体布局。从这种造型观念的一体性出发,美术品类的创作要求也是一体化的。陵园墓前石雕和墓室壁画、明器虽然有地层隔绝,主持设计者不允许它们同时展现于后世,但它们是要同时展现于可信的假设对象——灵魂面前的,它们有超时空的观赏者。在创作时它们依照一体化的墓葬观念和审美观念而雕刻、绘制、塑造,并各自行使着不同的表现职能。从设计指导思想出发,当观者(即鬼神魂灵)进入这个完整的造型世界时首先接触的是陵园茔域的建筑、雕刻,然后进入墓道、达于墓室,不断处在造型效果的包围之中,冤魂恶鬼会被驱逐,宾客神灵会被延入,墓主会得到完美无缺的保护和侍奉。从这个意义上讲,陵园雕刻、墓室绘画、随葬明器是具有审美一体性而不可分割的造型手段,它在一体化建筑前提下构成观念上的整体直观效果而不完全是形式可视的直观效果,这种观念性整体直观效果只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体现而不追求长期观赏过程的形式整体性,或者说亦追求着在天魂灵鸟瞰观赏的形式整体性。这种创作过程中的一体性特征无疑是相当重要的造型特征,?这也是陵园石雕部类设计思想的首要因素。
前面所述的风水堪舆理论与观念对陵墓范畴的美术尤其地面造型有着相当积极的影响,这就是对自然环境美的巧妙利用,即所谓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和谐,也就是陵墓总体融入自然的造型一体性。唐代及以前的风水堪舆理论对墓葬择地有许多具体要求,如所谓择山要求“山连百里不断,嵯峨有弯曲”,“山如卧蚕,从山似连珠”,“徘徊远望,山势似龙形”,忌逆山、断山;石山;择地要求朝夕见阳光,“从日出至没不见光者大凶”,忌“水无出处”、“四边有道”等(《永乐大典?大汉原陵秘葬经》)。对山水的要求是以“朝揖有情为贵”(《古今图书集成?青囊海角经》)。唐代对营葬择地当然重视,《历代陵寝备考?卷二十八》转述:“惟是当时各冢各有穹碑,夹以苍松翠柏、巨槐长杨、下宫寝殿,与表里河山共成形势”。表明了古人对墓葬环境的理解与重视。杜甫有诗咏桥陵:“先帝昔晏驾,兹山朝百灵;崇冈拥象设,沃野开天庭”;金城蓄峻趾,沙苑交迥汀。永与奥区固,川原纷眇冥”''“。他从诗人的角度阐发了同样的认识,而且具体点到了石象生与山冈的审美联系。唐陵修造虽有严格规范,但各陵茔域并不完全相同,一般根据山原地势周围环境而有所变化。例如桥陵的围墙并未保持方正的结构,而是依照山势起伏变化作了外形调整。可以说,陵园营造者在接受营造任务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利用自然环境美,在此前提下进一步协调陵园造型、墓室造型的一体化设计,在这种设计主体确立后才考虑到每项具体创作。
综上所述,唐陵所完善的陵园石雕艺术的设计特殊性体现在陵墓美术体系的设计思想所考虑的自然环境、陵园茔域、地上地下、墓室内部立体交融的审美一体性,各造型部类互相依赖,共同构成最终完整效果,陵园石雕在这个整体中有自己明确的位置。这一设计法则有深厚的观念意识作为活力,有对一体性的充分把握,这就要求我们对它的认识不能不是整体的、全面的、多层次的。
2、多层次造型意念
在陵墓美术体系的一体化设计前提下,陵园石雕的造型意念基本体现了个体层次、群体层次、建筑层次和环境层次。
唐陵石雕作品的个体效果在前文已经展示,我们过去的研究在这个层次上已比较深入。石雕个体是造型的基本单位,也是每个制作工匠的直接入手处,它们各自依照特定的尺度在特定的位置表现着特定的题材含义,每一单体都提供了环绕审视的立体效果,侧面、背面都不忽略,这无疑是一种进步,尤其在人像方面。每一人物的面相、衣纹、服饰,每一动物的姿势、表情、毛发,基座的花纹、石柱的线刻、碑头的龙形等都是一刀一凿雕刻出来的,不仅渗透着工匠们的艺术感觉,也渗透着他们的技术经验。
石雕群体造型表现几乎从这一造型品类一开始出现就受到了重视,唐代以前已经采用了中轴线对称列置于神道两侧的组合态势。唐陵石雕群体造型体现了韵律、节奏的组合形式感,神道柱以直立细长形式开其端,并规定了队列间距,动物群则以横长形体的重复形成第二韵律次序,人像又以竖长直立形体的重复形成第三韵律次序,之后又有间距收缩的石狮是为第四韵律次序。重复,在通常的群体组合中是尽量避免的,而在唐陵石雕造型中却尽量运用这一法则。四门重复的石狮、并排重复的鞍马、多达十几对的重复的文武臣像以至两行对称重复的队列,它们的基本形体相同,尺度相同、动作相同,观者目光到处,不断是外形刻板的直立、直立、直立,……令人压抑的“冷形式”。这种重复是为了强化特定的审美感受,充分适应需要传递沉重心理感应的陵墓主题要求,观者在规定路线内行进时无不处在带有强制性的重复性造型物给予的心理压抑中。这种造型形式的现实心理基础是宫廷仪仗、百官队列(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的排列组合也是一种“造型表现”)给旁观者的感受,其造型表现基础是千百年来的多种重复性作品的经验,如秦俑队列代表的俑类群体建筑中的长廊结构等。唐陵石雕的重复是成组的,变化也是成组的。它将大群体分成小单位,以重复不变的个体构成组,以变化对比的组构成群,在单一化重复的同时又使人感受到韵律性变化。既符合特定心理气氛要求又符合群体造型形式美的追求。
唐陵石雕艺术创作另一个重要的群体造型特征是运动中完成的审美感受。两列平行的群体构成不是仅为了场面宏阔,因为横向展开的群体也许更有宏阔场面感。夹神道而列的各类组合设置体现了先后出现的次序、高低错落的搭配,达到了一种自始至终不断变化而形成的审美运动过程。即是说,陵园石雕造型表现的完整效果是要在审美主体的运动状态下完成的。这一运动过程在往与返的逆向运动情况下审美心理感受是两样的。以石雕群主体而论,审视者从神道柱端向北行进,不断通过几个韵律次序,到达石狮端而初步完成群体审美过程(广而言之,实际上审视者一进入陵园,甚至一进入陵园自然区就开始处于特定的审美心理状态)。审美主体在任何一件单纯作品面前无论怎样感受均无法完成这种审美过程,它要求审视者从第一件到最后一件完整地从运动中全部感受之后得到一种综合印象,这印象中有每一件作品的成份,却不限于所有作品成份的总和,而是超出了这个总和,因为这印象中有时间因素,有人的行动因素。如果把石雕群体作为一个完整造型审美单位来看的话,它是具有三度空间加时间的四度空间造型,其完整的心理感受只有当主体置身神道并处在定向运动中才能完成。只有在这种运动过程显示的伸延层次中每一单体的审美表现才有了完整的意义。这种审美表现特征与传统绘画中场面题材的散点透视法则具有相同的美学基础。
这里不应忽略的一点是,陵园石雕群审美过程性的最佳体现状态是处于祭陵活动的动态氛围中的静态情况。唐代象历史上的其它朝代一样,丧葬活动是重要的政治活动,这类活动尤其皇室规格是有仪仗吹奏内容的。据《唐会要?卷三十八》记,文武官员及庶人的送葬队列即有不同规格的“辆车”,“油幌,朱丝网络,两厢画龙”,“铎”,“黻篓”,“盾车、志石车,任画云气”,“方相车”,“魂车”,“鸟兽旗番”等并有专唱挽歌、“前后鼓吹”的人。浩浩荡荡、丰富多彩、鼓乐唱挽的队列进入护卫森严的陵园神道时,石雕群体给予活动者的过程性审美感受才达到了设计者所追求的最完善的效果。
唐陵石雕群是附属于陵园建筑总体布局同时又有其独立意义的艺术主题,它有自身的审美价值,却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作为紧凑的群体结构出现,却又是整个建筑格局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唐陵石雕群将主体设置于陵园南门神道,北门、东门、西门也有少量设置,总体形成对建筑中心的衬托护卫。它和陵台、寝殿、门墙、阙楼等一整套建筑形成节奏鲜明、变化丰富的完整格局,它自身又是建筑格局进伸演进中的特定审美阶段。如果说建筑在这里是生命环境的体现,那么石雕群则是生命人格的体现。从形式美角度看,石雕群是陵园建筑中的装饰性陈列,装饰作用无疑是它自身具有的重要特征之一。当伴随着音乐庄重缓进的祭陵队伍通过神道时,当守陵侍卫者一日三次供奉陵主时,当后世群臣瞻仰缅怀先王威仪时,它都要引起人们的直观美感,而这种美感是绝不能脱离建筑环境的。我们今天站在建筑已荡然无存的唐陵石雕面前的直观感受中已经失落了这种创作初衷,而在继承了其美学宗旨的明陵、清陵石雕面前尚能够在无知觉中使审美心理纳入建筑环境氛围。
将墓葬融入自然的观念客观上为陵园石雕艺术提供了可贵的自然环境审美效果,这在前文已经叙述。石雕创作者置陈布势之时在风水堪舆理论指导下对山川地貌的具体利用是显而易见的。陕西唐十八陵集中于关中盆地北部,南临渭水,北依高山,造成帝王君临的大气势,取境壮阔。建筑类型分覆斗型与山陵型两类。前一类往往位于高原边缘,神道尽头即是河川盆地,冢堆耸起后大有高屋建瓴之势。从原下望去,陵园拔于高原断壁之上,十分壮观。而石雕群正位于断壁边缘地带,以最南端的神道柱为标记,顺势向内伸延。后一类也是后代多相延续的一类,依山为陵,形势更为壮美。陵址按风水要求而选择在山势呈扇面形烘托的山腰中,神道顺坡势伸延,远方关中大地、谓水一脉纵览无余。石雕群设置根据具体地貌环境南低北高,逐渐上升。有的夹沟壑而列,场面宏阔(如建陵);有的立于坡脊,充分利用山势高拔(如乾陵)。唐陵选址和“风水”效果各不相同,但有同一宗旨,即地处高原,依山面水,峻拨开阔,集大自然中高山、大河、广原的壮美,从而使它形成了历史上独步百代的陵园石雕艺术阶段特征。即使在建筑荡然无存的今天,两列斑驳的青石一座风水佳胜的山陵便足以体现出我们开篇所见到的那种盛唐气象。
环境层次的另一个要素是环境的变化效应。“风水”有天、地两部分构成因素,“风”代表着天的运动,有四季变化、阴睛朝夕变化、风云雨雪变化;“水”则代表着地的运动,有草木枯荣变化、溪流涌涸变化,甚至淙淙水声也属于审美总体效果的一部分。石雕群的环境效果是不断变化的,当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条件下登临乾陵或经过桥陵或步入建陵时审美感受是丰富多彩而多样统一的。这里叙述的景观变化效应不是我/门今天单方面的理解,而是设计者从一开始就全力追求、统筹考虑的。“风水”关系在这里不仅仅是环境关系,而且蕴含着人工与天工的内在联系。在先民心目中,石,是永恒的造型材料;山,是永恒的自然形象;土木可湮而石不可湮,殿堂可毁而山不可毁,石取诸山而山择诸自然。人,同为自然的一部分,将自己的肉体、精神、理想、情感通过山、石融于自然,合为一体。简单的石雕、山势之中被赋予了人的观念,使之脱离了单调的地质符号而升华为载负着情感的有内在联系的审美对象,在特定的造型意义上获得了人的生命,得以使构成之初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直至今日凝聚不散。融合于人为选择改造的环境中的石雕群被赋予超出雕塑作品自体的魅力。在这个高层次的升华中,风水堪舆理论提供了完整的思想,从而支撑了陵园石雕艺术生命力历久不衰的基础。
在陵园石雕艺术的环境——建筑——群体——个体这种多层次的造型意念指导下,创作者首先考虑的是环境层次,其次是根据精心选择的环境的特征巧妙布局建筑和石雕群,再其次是设计群体配置、组合效果,最后才着眼于每件石雕作品的具体处理效果,这个具体效果是必须服从前三项要求并主动体现一体化多层次创作精神的,这是在几千年发展的墓葬观念、造型观念制约下顺理成章的导出自然地贯穿于设计者和制作者的认识深层。
结论
唐代陵园石雕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那种自由洒脱、矫健华美之风而走向恢弘壮伟、高贵厚重。它寄托着统治阶级的天命观、世界观,体现着他们的墓葬观念和审美观念。高度秩序化的时代趋势造就了陵寝制度在新的层次上的复兴,造就了陵园石雕群的设置序列、造型规范和审美倾向。
随着宗教石雕艺术的迅猛发展,陵园石雕以整齐严整的序列和空前数量的设置、高屋建瓴的气象崛起于唐代造型领域,由于它具有鲜明的民族本土意识、奇妙的观念综合显现方式、特殊的审美意义,因而从唐代形成了完备的表现形式和大规模的时代延续性,并在前代基础上和地下墓室雕刻、明器雕塑共同发展成为区别于由外来题材形式发展起来的宗教雕塑的又一大古代雕塑系统。溯其渊源,起自战国,奠基于汉晋南北朝,扩展于五代、宋、明、清。以崇山峻岭为景深屏障,以关中平原为平面依托,以陵园总体为中心基础的唐陵石雕艺术正处在这个大系统的宏观转折点上。
唐陵石雕艺术在陵墓雕刻史上乃至美术史上的历史性意义一是它的开拓性,一是它的禁锢性。二者是具有实际内涵的相对存在,也是与前朝后代的根本区别。唐陵石雕艺术主旨的多因素综合显现方式代代相延、不断强化,其制度化趋势、王权等级观念、歌功颂德和征服海内的造型需求愈演愈烈。其设置内容、技巧规范、组合形式等也被后代广泛延续。其所完备的一体化设计思想、多层次造型意念及审美过程性、环境艺术观等体外构成的美学内容在后代得到了发扬光大。唐陵石雕打破了前代的样式限制而展示了崭新的气象,结束了前代无序的表现阶段,开启了制度化程式化表现阶段。具有鲜明的转折开拓意义。
另一方面,在封建社会的特定局限中,唐陵石雕提供给后代一种完善的造型形式、同时也是禁锢性的造型形式,规定了这一特定造型品类的群体和个体表现方式、雕刻群和建筑群的组织方式、内容配置构成方式及至造型的一系列具体规范,将艺术引向程式化,阻遏了早期自由无序的传统的发展,全面开始了写实模仿性的审美倾向。我们所注意到的后代陵园石雕的全面模式化特征主要缘于唐陵的归结。诚然,唐陵石雕的造型程式不能强加给后代,但禁锢的社会形态、制度形态、文化意识形态千年不变的状况决定了这种最佳艺术语言的禁锢性。





您可以选择一种方式赞助本站
赏